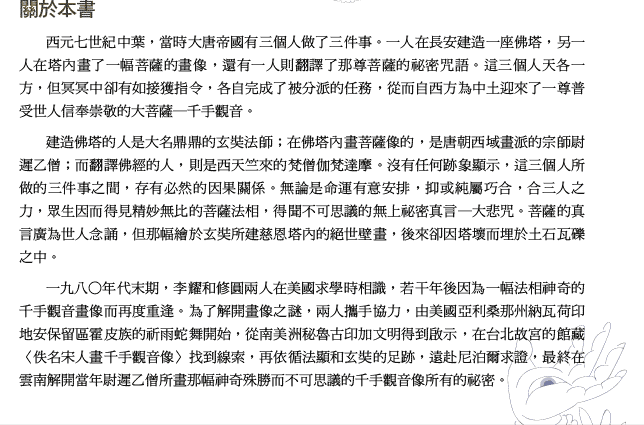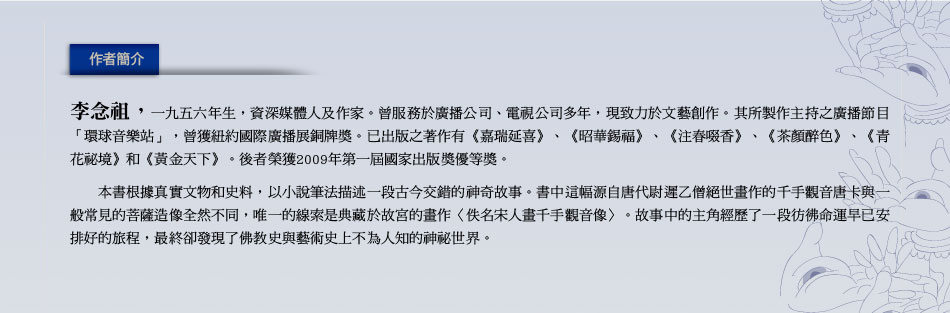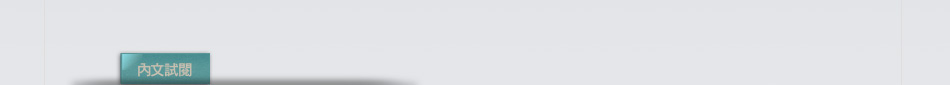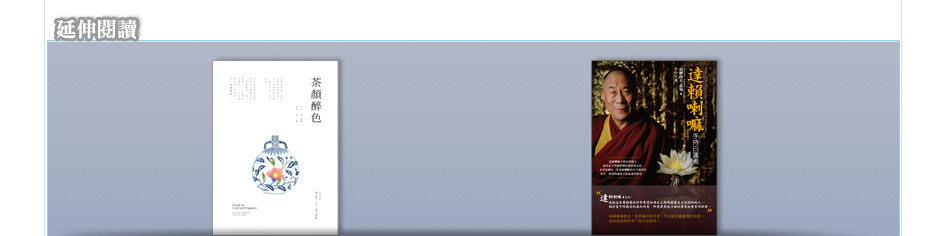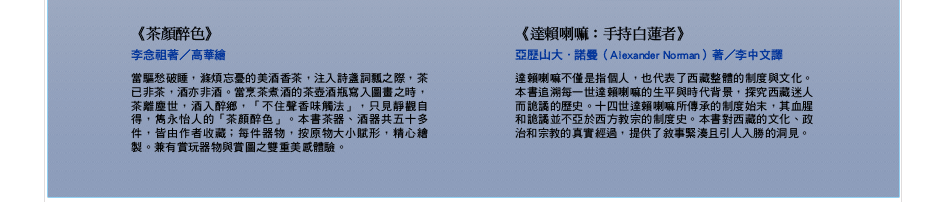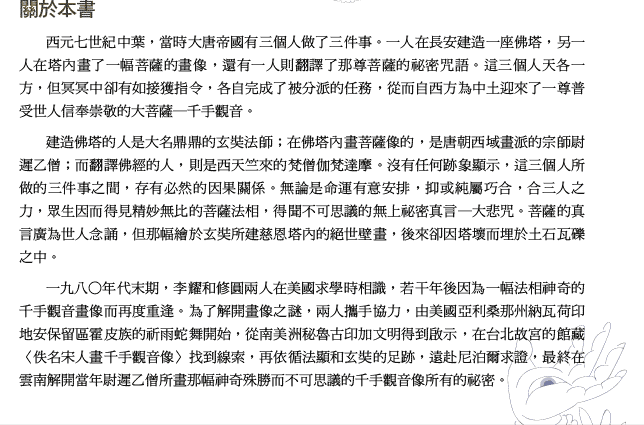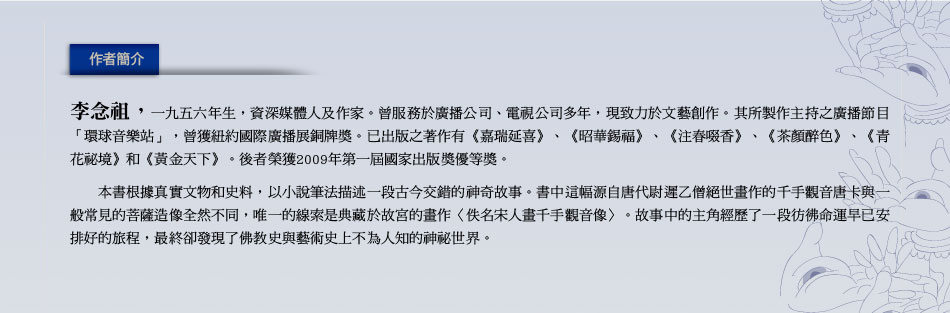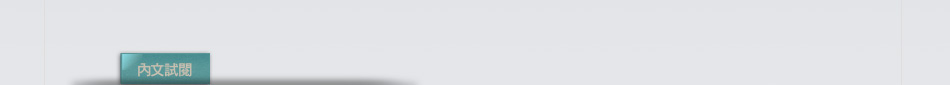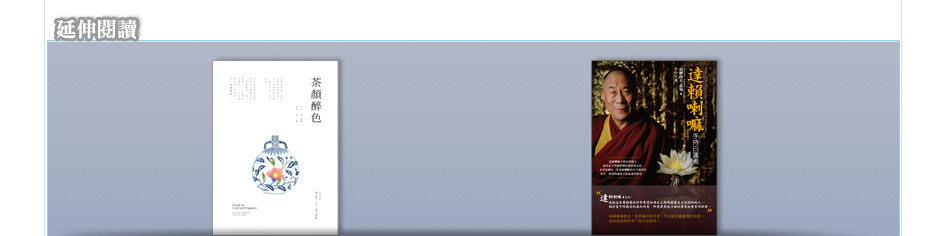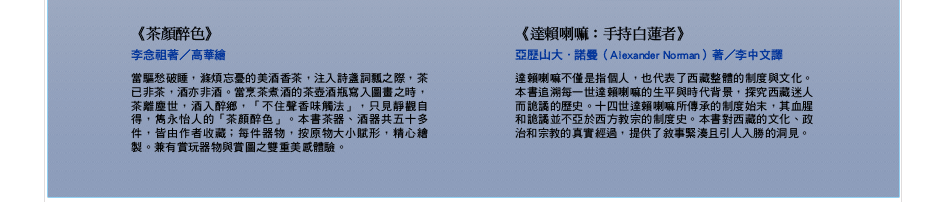第一章 祈雨蛇舞
巫師終於進場了,氣氛神祕詭異而嚇人。
雖然修圓事先心裡早已有所準備,知道自己即將看到的是非常駭人的場面,但真的親眼目睹時,仍然驚異莫名,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這樣游走在生死邊緣的「舞蹈」。
帶頭的巫師穿著短裙,披頭散髮,上身赤裸,身上畫了許多白色、紅色和褐色的線條,胸前掛著獸牙串起的項鍊,蓬鬆的頭髮和插在上面的一堆羽毛糾結在一起,看上去像一團亂草。巫師的嘴裡咬著一條幾乎有手腕粗細的蛇,蛇身頭尾在巫師臉部兩側不安的扭動,三角形的蛇頭和一截環形的蛇尾,一望而知這是劇毒的響尾蛇。
跟在巫師身後進場的還有五名印地安勇士,同樣也穿著短裙,披頭散髮,赤裸上身,只是頭上沒有羽冠,胸前也沒有巫師佩帶的那一串誇張的獸牙項鍊。和巫師一樣,這五名勇士每個人嘴裡都咬著一條蛇,踩著抑揚頓挫的步伐,在四周印地安人低沉的吟誦和規律的鼓聲節奏中,繞著圈子來回踱步。
這五名勇士和帶頭的巫師每個人身旁有一位同伴,手裡拿著一把羽毛帚,隨著隊伍一同前進,只要一發現蛇頭有昂起的跡象時,就用手中的羽毛帚遮住蛇頭往下壓,防止蛇回頭咬人。
跳蛇舞的印地安人行進的方式非常奇特,時而向前,時而向後,有時往左橫移,有時又往右跨步,彷彿遵循著排練已久的舞步節拍。不過因為他們行進間的速度時而慢,時而快,使得修圓雖然很專心的想要記下這些印地安人的步伐節奏,但始終難以確實掌握他們舞蹈的旋律和脈動。
慢慢的修圓發現,引導巫師和這些勇士行進的並不是一種固定的步伐,而是環繞在他們四周所有印地安人忘我的吟誦混合著鼓聲所形成的一股奇異聲浪。一波接著一波,連綿不斷的吟誦就像是西藏喇嘛們坐在大殿上集體誦經的梵唄。巫師和那五名勇士的動作就是受到這股奇異聲浪的牽引,舉手投足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動靜一致的和諧節奏,宛如有人在前面指揮一樣。甚至那些被巫師和勇士們咬在嘴裡的響尾蛇,似乎也受到這股奇異聲浪的催眠,在整個舞蹈儀式進行中,馴服的任由巫師和勇士咬著,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的移動,沒有製造任何驚險的場面。直到一名勇士在經過修圓面前的時候,腳下突然一滑,身體失去平衡,結果那條他嘴裡咬著的響尾蛇,蛇頭原本就離他的臉很近,突然間受到驚擾,在所有人都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一張口就咬在勇士的脖子上。
「啊……危險!」
就在修圓看到響尾蛇張開大口,露出兩根尖銳的蛇牙,向那名印地安勇士一口咬下去的時候,自己也被嚇的後退,發出一聲驚叫,跌入地下的一個黑洞。修圓一身冷汗的在黑暗中呆坐了半天,直到意識全部恢復,才確定自己剛才只是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
連續兩天做相同的夢,這種情況真的很不尋常。修圓平常總是一覺到天亮,很少作夢,即使偶爾作夢,也從來沒有作過相同的夢,更不用說是這麼可怕的夢了。聽說夢到蛇表示會發財,不過那條響尾蛇的樣子如此兇惡,怎麼看都不像會帶來財運,不出什麼意外就阿彌陀佛了。
夢到如此詭異的景象,想不理會,繼續再睡,已經是完全不可能了。
修圓泡了杯茶,在書桌前坐了下來,桌上攤著一堆散亂的文稿資料。最近一家出版社來邀稿,希望修圓把他在廣播節目「大千世界」裡面所播出的節目內容重新整理潤飾,結集成書出版。為此修圓除了翻出做節目時留存的筆記摘要,也特別去圖書館查考相關的資料。寫書畢竟和主持節目不同,不能隨興所至,天南地北的閒聊,一切得說清楚,講明白,有個確切的交代。
「難道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修圓喃喃自語,目光落在桌上那本從圖書館借回來的《山海經》和過去曾經在節目中報導過的「印地安蛇舞」那一集的手寫文稿上。
修圓這兩天所夢到的景象,並非潛意識中離奇荒誕的畫面,而是六年前在美國曾經親眼看過的印地安蛇舞。夢中所見不是虛幻的情節,而是真實事件的倒帶。唯一不同的是,當年看蛇舞的時候,整個過程非常順利,並沒有發生夢中毒蛇噬人的情況。
※※※
蛇舞是亞利桑那州納瓦荷印地安保留區內霍皮族傳統的祈雨儀式,其歷史和霍皮族人的存在一樣久遠。舉行這項祈雨儀式的前幾天,來自霍皮族幾個部落的巫師會帶著他們的助手去野外捕捉有劇毒的響尾蛇,然後裝進一個大袋子帶到舉行儀式的地點,把蛇集中放在一個土坑裡,由專人看守。儀式舉行完畢之後,再由專人把這些捉來的蛇送回原處放生。
霍皮族原本每年都舉行跳蛇舞的儀式,也不禁止外人參觀,後來改為兩年一次,而且不再對外開放。修圓在美國讀書時有機會看到印地安霍皮族的蛇舞,完全是因為同校一位不同系所的同學李曜的主動邀請。
李曜是華裔新加坡人,英文名字叫Victor,他是修圓在美國讀書時同寢室的室友。修圓讀大眾傳播,李曜唸藝術史,或許是因為兩人都來自亞洲,都講中文,因此所學雖不相同,但卻很談得來,相處非常融洽,甚至一九八八年趁耶誕節學校放長假,兩個人還一起結伴到秘魯去旅行。
一九八九年暑假,修圓提早結束「非法」的暑期打工,提前返校,準備開始撰寫畢業論文。當時每一位來美國留學的外國學生,美國政府會發給一張社會安全卡,上面特別加印「不得工作」的字樣,不過很多台灣和大陸來的留學生在寒暑假期間還是無視禁令,總會設法找份短期工作,賺一點生活費。
李曜家境好,用不著去打工。修圓則不然,必須靠暑期打工的收入貼補下學期的生活費。修圓的運氣不錯,從報紙的分類廣告上找到加州大熊湖附近一間中國餐館端盤子的工作。那裡風景很好,觀光客很多,餐館的生意也很好,要不是為了寫論文,修圓原本是打算多做幾天的。
修圓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放棄打工賺錢的機會,提前返校。沒想到才踏進宿舍大門,李曜就像颳龍捲風式的衝過來,說他已經取得亞利桑那州納瓦荷印地安保留區霍皮族人的同意,正準備出發前往當地觀看霍皮族神秘的蛇舞祈雨儀式,還擺出蛇拳的招式,模仿蛇昂首吐信的樣子。平常李曜的行為舉止總是非常優雅,個性也很沉穩,修圓幾乎不曾見過李曜對人或對事出現這種熱切渴望,坐立難不的表情舉動。
李曜所說的蛇舞這件事一定很不尋常,這是修圓做出的結論。修圓還來不及問蛇舞是怎麼回事?也來不及放下行李,已經被李曜拖上車,一路從加州跑到亞利桑那州,進入巨岩、峽谷、砂礫和散落著灌木叢的印地安保留區。
可能是因為這是修圓第二次接觸美洲的印地安人和印地安文化,所以感覺上並不如去年第一次和李曜去秘魯那樣,對眼前所看到的南美洲印地安世界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與好奇。特別是在的的喀喀湖畔遇見的那位薩滿巫師和在納斯卡搭飛機從空中看到的神祕納斯卡圖形,那種奇特、陌生、原始、神祕的經驗,完全不同於修圓以往生活的世界。修圓在秘魯所目睹的一切,不折不扣,是一次空前的文化震盪。不過等到修圓親眼目睹霍皮族巫師嘴裡咬著響尾蛇出場,才知道自己真是大錯特錯。秘魯之行確實讓修圓開了眼界,但霍皮族蛇舞才真的是「震撼教育」。當時修圓雖然只是在場邊觀看,距離跳舞的巫師還有十幾公尺遠,但總覺得自己脖子上涼颼颼的,好像蛇的鱗片就在頸項間滑動,渾身都不自在。
修圓坐在書桌前面,想了半天,覺得最為不解的也正是這一點。因為即使當時親身經歷那樣駭人的場面,晚上入睡時也不曾因此做過什麼噩夢,沒有夢見巫師,也沒有夢見可怕的響尾蛇。
「為什麼事隔這麼久,會連續兩晚夢到同樣的景象?是有什麼事即將發生的前兆嗎?還是因為自己這兩天整理資料,驚擾到塵封在記憶中的毒蛇?抑或是古書中記載的雨師妾真的和霍皮族蛇舞有所關聯,所以印地安巫師和那些響尾蛇才會出現在夢境之中?」修圓的目光再次停在桌子上的那本《山海經》。
修圓會去翻閱這本現代幾乎已經沒有人會提起的先秦古籍,本來是準備在要出版的書裡面稍微談一下古人所認知理解的世界概況,不料卻意外的在〈海外東經〉這一章看到古代遙遠的海外東方有所謂的「雨師妾國」。如果從今天亞洲的角度來看,這個雨師妾國無疑是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陸。《山海經》所說的雨師妾國,那裡的人長相非常詭異,左耳上有青蛇,右耳上有赤蛇。這要是以前,修圓一定把它看作是古人怪異荒誕的無稽之談,再不然就是像蛇髮女妖梅杜莎之類的神話,絕對不會認為世界上真有這麼回事。
霍皮族為祈雨而跳的蛇舞,改變了修圓的看法。所謂雨師,不就是祈雨的巫師嗎?妾是女子的稱謂,那些霍皮族的巫師和勇士披頭散髮,穿著短裙,看起來的確是女人的樣子。而他們嘴?咬著響尾蛇,蛇頭和蛇尾在臉部兩邊扭動,遠一點看,果然也很像左耳、右耳都有蛇的「雨師妾」。記得李曜曾經提過,美洲的印地安人最初來自亞洲,這個說法看來是有道理的。最起碼,在遠古時期,亞洲和美洲的居民是有所接觸的。《山海經》有關雨師妾的描述,如果沒有事實基礎,只憑想像,恐怕很難編出那麼具體的細節。
事實上修圓對霍皮族的蛇舞會記得那麼清楚,除了蛇舞本身場面震撼駭人以外,李曜當時所提出的一個完全不搭軋的奇怪問題,更加深了修圓對蛇舞的印象。修圓這兩天邊寫稿邊回憶當時的情景,自己都不禁感到訝異,雖然去納瓦荷印地安保留區看蛇舞這件事距離今天已經有六年之久,但當時所看到的一切,不僅沒有遺忘,而且很多細節還格外鮮明。李曜在跳蛇舞的儀式結束之後,突然問他的那個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你有沒有唸過大悲咒?」李曜說話的語氣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認真。
「算是唸過。怎麼?和霍皮族的蛇舞有關嗎?」除了蛇舞,修圓想不出李曜何以突然會問他這個問題。
「那你知道大悲咒的內容在說什麼嗎?」李曜沒有正面回答,反而繼續再問。
「以前清明、中元舉行法會時,我偶爾跟著廟裡師父念誦大悲咒。前面的祈願文很容易理解,但咒文就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為此我還特地問過師父,師父只是說這是用漢語拼寫的梵音,是觀世音菩薩的祕密真言,不必有特定的意義。」修圓就自己所知如實回答。
「我不能說那位師父說的不對,不過如果把漢字所譯的咒語還原為梵文,那八十四句的大悲咒其實是有意義的。」
修圓雖然覺得李曜此刻提大悲咒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但李曜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不像是隨口說說。
「真的啊!那裡面說的是什麼?」修圓順著李曜的話問。
「主要是讚美和禮敬觀世音菩薩,然後強調要堅持作為,遠離束縛,趕快行動,征服、往生、覺悟、解脫等等。」李曜顯然對大悲咒的內容相當熟悉。
「這些語句雖然有意義,不過聽起來似乎確並沒有針對什麼特定的人和事而言。」修圓表達自己的想法。
「人和事是沒有,但菩薩卻有。」李曜指出問題的重點。
「你剛才不是說在讚美和禮敬觀世音菩薩嗎?」修圓有點不解。
「是觀世音菩薩沒錯,但卻是一尊很特殊的觀音。」
「什麼特殊的觀音?」
「青頸觀音。」
「青頸觀音?」修圓還是第一次聽到有這尊菩薩。
「這是觀世音菩薩諸多化身之一,這尊觀音和平常我們看到的諸如水月觀音、白衣觀音、魚籃觀音等等最大不同的地方……你猜猜看是那裡?」
「這還用猜!顧名思義,當然是菩薩的頸部。」修圓心想如果菩薩頸部不是青色,那幹嘛叫青頸觀音?
「沒錯,青頸觀音和其他觀音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青頸觀音的頸部是青色的。」
「我猜這一定有什麼典故?」
「是有典故。據說青頸觀音是為眾生受毒,所以頸部呈現青色。」
修圓對青頸觀音一無所知,不過修圓很清楚李曜不會在看過蛇舞之後,無緣無故的又提大悲咒,又說青頸觀音,這件事肯定跟霍皮族的蛇舞有關。修圓沒有料錯,只是沒想到光是「青頸」這個字眼,李曜就解釋了半天。
李曜說「青頸」一詞其實源自印度教的濕婆神,是濕婆的另一個名字。根據印度的神話傳說,眾神雖然擁有凡人所無法企及的神力,但仍然不能免於生老病死的輪迴,於是眾神決議齊心協力,用宇宙最高的須彌山去攪動乳海,調製長生不老的靈藥。問題是須彌山太大,眾神得用繩子把山綁起來,才有辦法攪動乳海。這根繩子不是普通的繩子,世界上也沒有這樣一根繩子,只有巨蛇舍沙可以像繩子一樣把須彌山纏繞起來。就在眾神合力抓住舍沙的尾巴,費盡力氣將須彌山在乳海中攪拌,大功即將告成之際,舍沙忍受不住身體的劇痛,口中噴出大量毒液。眾神眼看大家千辛萬苦,費盡心血煉製的靈藥一旦沾到毒液,即將前功盡棄,因此趕緊向神通廣大的濕婆神求救。濕婆的辦法很簡單,他將毒液全部都吞下去,就把問題解決了。不過當吞入的毒液流過咽喉時,劇烈的蛇毒使濕婆的頸部變成了青黑之色,從此濕婆有了另一個名字「青頸」。